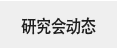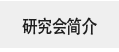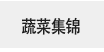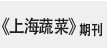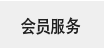粮安天下,种为粮先。正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上海,如何用好科技资源密集优势,助力攻克种子“芯片”?
《上海市种子条例》经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其中专设一章强调“种业创新”。“上位法中关于种业创新的表述分散于各章节,此次地方立法集中归并后专辟一章,就是为更好激励种业科技创新。”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放眼全国,按照育种水平和种源竞争力,种业发展总体呈橄榄型分布。“橄榄”顶部是有优势的种源,如水稻、小麦两大口粮,育种水平和单产水平居于世界前列,种源完全自给且有较强竞争力;“橄榄”中部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有差距的种源,如玉米、大豆、油菜、马铃薯和大田蔬菜等,种源基本自给,但在产量和质量等方面仍有待提升竞争力;“橄榄”底部是大量依靠进口的种源,如甜菜、个别食用菌等,其种源选育在国内基本处于空白。
在这场种业翻身仗中,缩小差距、补齐短板,势必要靠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此次地方立法正是为破解限制创新的种种瓶颈,激励社会各主体开展联合育种攻关,培育经得起市场考验的新品种,立足科创中心建设优势,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新跨越,推进上海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
“板凳坐得十年冷”常用来形容基础研究,种源研究的等待期更漫长。
“以水稻繁育为例,最快要6至8年才能选育出新品种,如何确保稳定的科研支持?”调研中,不少专家学者直陈困扰许久的顾虑。种业研究中,科学家们的启动资金常源于国家科研项目,支持期一般为五年。一旦期满,科学家就要自寻出路。只有找到接续资金,才能确保前期研究不会“打水漂”。

从实践来看,应用性较强的科研项目有机会找到社会资本作后盾。然而,对于更偏向基础研究的种质资源收集保存项目来说,长期稳定的支持“可遇不可求”。《条例(草案)》公开征询意见时,数百条建议直指建立长期稳定的科研支持机制。为此,《条例(草案)》在二审中新增“种业创新公共服务”条款,明确推进公共服务相关平台建设,促进资源开放共享。
“种源农业是交叉型学科,涵盖农学、机械工程等领域,开放平台能让科学家便捷地获得科学仪器设施,加速联合攻关。”上海海洋大学教授王成辉解释,实验中需进行基因测序。然而,这类设备不仅需“量身定制”,同时耗资不菲。如有专项资金能定向扶持建设相关平台,就能提高创新效能,产出更多公益性研究成果。
千辛万苦育出良种,更关键的是如何在田间地头复制推广,让创新成果惠及百姓餐桌。
据初步统计,全国目前已审定的种源品种达上万个,其中真正走通市场的仅数千个。相当于80%的创新成果还被锁在实验室,种源创新面临转化难。

“长期以来,种业和其它领域一样,科研单位育种与市场脱节,存在科研与生产‘两张皮’问题。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能整合企业与科研单位的优势资源,取得‘1+1大于2’的效果。”市农业农村委种业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解释,强调商业化育种是《条例》创新内容之一。《条例》明确支持种子企业开展商业化育种创新,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共设研发基金、共建实验室、组建创新联盟等,开展种业自主创新和突破性品种选育。
近年来,上海涌现出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的本土企业。然而,不少企业仍面临多而不优、多而不强等难题。去年,农业农村部公布国家农作物种业阵型企业名单中,上海有3家企业入选“破难题阵型”。未来,这些企业将瞄准种业创新“头雁”的目标,在菌菇、甜菜等少数主要依靠进口的种源领域孕育创新良种,助力打好种业翻身仗。
激发科研机构、种源企业创新动力,知识产权保护是关键。
借鉴上位法的经验,《条例》引入“实质性派生品种”这一概念。通俗理解,它是指对一个育成品种进行修饰改良后选育的衍生品种。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叶片颜色等细微处有区别,但在亩产量等关键核心指标上无明显差异。
“如果放任修饰性创新成果抢占市场,就会挫伤企业、科研机构进行原始创新的积极性。”《条例》明确提升实质性派生品种管理,提升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这意味着,一旦被定性为“实质性派生品种”,企业要在商业化销售中将部分收益反哺给原始创新品种的研发单位,共享利益。
规则明确,还要夯实管理职责。过去,种源保护的责任通常落在农业部门。然而,认定实质性派生品种颇具含金量,涉及DNA分子检测、新品种测试等。《条例》指出,知识产权等部门应当为植物新品种权等种业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等活动提供指导和服务。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陆峥嵘表示,将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坚持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标本兼治,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行政等多种手段,推行全链条、全流程监管。
《条例》还明确健全种业科技成果权益分配机制。此前试点中,上海部分科研单位已与种源企业形成一次性转让、按比例合作等方式。部分手握原始创新成果的科研机构,不仅能从“一锤子买卖”中获得可观收益,更能从高附加值技术服务中收获长期稳定的效益,反哺创新。